推文信息
图片来源:https://jx.people.com.cn/n/2014/0312/c355203-20759227.html
原文信息:Claudia Goldin, Joshua Mitchell, “The New Lifecycle of Women’s Employment: Disappearing Humps, Sagging Middles, Expanding Tops”, NBER working paper, No.22913, 2016.

距离1955年毛主席提出“妇女能顶半边天”的口号已经过去了60年,而今,全球范围内的女性劳动参与都呈现出“蒸蒸日上”的势头。与男性的劳动供给不同,女性的劳动供给在整个生命周期中更容易受到经济发展和非经济因素的影响,所呈现的特点比较复杂。
今天推送的这篇文章是Claudia Goldin在NBER的一篇工作论文,Claudia Goldin是哈佛大学的经济学者以及QJE的编委,她长期关注女性就业问题。这篇工作论文使用HRS和SIPP等数据对美国女性的就业生命周期进行了世代追踪,发现了从50后一代(恰巧也是1950年之后——然而仅仅是个巧合)开始女性就业生命周期曲线呈现出来的新特征。作者并没有使用繁复的计量分析,仅有的回归也只是报告了结论,对于关注因果识别方法的看官们简直轻松得像劳动经济学教科书,但其剥洋葱式层层递进地从数据的各个剖面寻求证据的做法体现了作者精巧的研究思路,应该可以称之为描述性分析中的“样板戏”了。
1
最主要的发现
新的女性就业生命周期出现于50后一代:女性刚刚毕业时,高的劳动参与率将持续10年左右,当30+或40岁多一点时,劳动参与率开始下降,称之为“中部凹陷(sagging middle)”;此后,劳动参与率略有上升,直到在60+之后不再工作(图1)。从可观测的样本来看,女性在老年时期(六七十岁)的劳动参与率已经有了很大的提高。因此,新的就业生命周期曲线总体上看起来相对更高且平坦。
然而,在此之前情况却完全不同:20-50岁,女性劳动参与率是不断上升的,50岁时开始下降,直到退出劳动力市场。也就是说女性就业生命周期呈现倒U型——或称之为“拱形(hump)”。
我们对女性就业生命周期曲线的最佳预测是:进入劳动力市场初期,劳动参与率高,之后呈现出一定程度的“中部凹陷”,然后是缓慢的回升,且逐步退出劳动力市场的过程将更加漫长——在就业生命周期的尾部有一个“延长的高峰期(expanding top)”。劳动参与率在女性的整个生命周期中都将更高,并且开始和男性的就业生命周期有点相似了。
“中部凹陷”和“延长的高峰期”共同导致了一种“扭转(twist)”现象。通常来讲,年轻一代的劳动参与率比前一代高,女性的就业生命周期曲线按照世代递减排列,最年轻的一代在最上面。但是近年来,女性仅在20-30岁仍遵循这样的规律,而等到她们步入中年,最年轻一代的劳动参与率竟然开始低于前几代了(图1)。
“中部凹陷”和“延长的高峰期”都很有趣。“中部凹陷”使得人们关注并对年轻女性单方面辞职持负面意见。“延长的高峰期”引起了对年长女性高就业率的讨论,持积极态度的人们认为这是因为年长女性正变得身体更健康且更享受工作,持消极态度的人们认为这是因为她们没有足够的财富支持她们安享晚年。
2
来自数据的佐证:累积工作年限与劳动参与分布
作者首先从累积工作年限的角度寻找“中部凹陷”的佐证。
最开始的一代(1935-1939)在整个就业生命周期(25-54岁)内累积工作年限仅为15.6年,而最近的一代(1955-1959)这一数字为22.2年(图2.A)。这一变动的近一半可归因于她们在就业前10年(25-34岁)的累积工作年限变动(图2.B)。
将就业生命周期的30年平均划分成三个时间段,每一段10年,观察在每个10年中的累积工作年限的分布情况,如图2.C。对于1935-1970年之间的世代,第一个10年(25-34岁)累积工作年限发生了大幅的上涨,而第二和第三个10年的累积工作年限上涨仅仅存在于早期样本(1935-1950年的世代)中。这为“中部凹陷”提供了侧面的佐证。
然后,作者又试图从劳动参与分布中寻求女性就业生命周期变化的证据,在这里使用了两个“尾部”指标:劳动参与率高于80%的人所占比重,以及劳动参与率低于20%的人所占比重。结果发现,不论是对于整个就业生命周期(25-54岁),还是对于生命周期的前10年(25-34岁),女性劳动参与率都有相同的变化趋势:工作时间高于80%的人越来越多,低于20%的人越来越少(图3)。
此外,控制世代、教育和子女数量进行回归发现,年轻时期劳动参与率高的人,随着年龄增加她们的劳动参与率依然高。此外,作者的另一篇论文得出结论:一个年轻期劳动参与率高的人,年长期(59-63岁)的劳动参与率也较高。这或许可以为“延长的高峰期”提供佐证。
使用HRS的数据,控制了世代、子女数量、教育水平和种族,并加入母亲年龄的二次方进行回归,得到另外一个有趣的结论是:当第一个子女出生(约25-30岁)时,伴随的是女性在25-34岁的劳动参与率上升和35-44岁的劳动参与率下降。这就是说,第一次生育年龄的推迟很可能是女性就业生命周期“扭转”的重要原因。
3
寻找“中部凹陷”的原因:生育和生育保障制度
毋庸置疑,子女数量和生育年龄的变化是女性就业生命曲线变动的重要原因。
从数据来看,婴儿潮一代的母亲(1935-1944年一代)在第一次生育后劳动参与率急速下降,且之后十年都没能恢复到育前水平。然而对于之后的1945-1949一代来说,生育前的劳动参与率比上一代人更高,且育后十年内劳动参与恢复到了育前水平,对于1950-1960一代,更是如此(图4.A)。
拥有大学学历的女性,1945-1949和1950-1954两代人的劳动参与在生育后十年内恢复到了育前水平,而之前的世代并没有,这和全体女性样本所呈现出来的状态是一样的。但这里出现了新的趋势:1954年之后的世代的劳动参与率并没有在育后十年恢复到育前水平,而且1960-1964一代的育后劳动参与水平比1955-1959一代还要低(图4.B)。因此,可以明显看到“中部凹陷”大约始于1955一代。
既然生育能部分解释“中部凹陷”的出现,那么生育保障制度会不会强化这种效果呢?作者探索了怀孕期间的离职状态(带薪休假、无薪休假或辞职)对女性首次生育前三年后十年劳动参与情况的影响(图5)。结果发现,在生育前三年和后十年,带薪休假的女性劳动参与率最高,无薪休假的女性其次,劳动参与率最低的是那些在生育期间辞职的女性。因为无法知道哪些因素决定了女性落入“带薪休假”、“无薪休假”、“辞职”的类别中,关于带薪休假政策如何影响女性就业就无法得到确定的结论。但是可以明确的是休假和延缓退出能够提升生育后的就业率。*最后一句不说自明
4
世代效应(cohort effect)与年龄效应(lifecycle effect)

作者认为,世代效应在1950年之前的世代中曾影响很大,甚至超过了年龄效应(或称之为“生命周期效应”),从而导致了倒U形的女性就业生命周期。而“中部凹陷”的出现是因为世代效应逐渐减弱,年龄效应自50后和60后一代开始凸显。与之前的世代相比,50后和60后晚婚晚育的比例开始升高,一部分人在中年辞掉工作,之后再返回劳动力市场,并且在晚年时将会维持更高的劳动参与率。
5
最后的讨论
新的女性就业生命周期出现了,那么到底是什么导致了这种变化呢?关键的几大要素有工作本身的变化、事业的兴起、女性受教育水平的提高以及晚婚晚育。“中部凹陷”有可能来自美国带薪休假制度的短期效应。从国际对比来看,那些有着更宽松休假制度的国家(如奥地利、丹麦、挪威和瑞典),女性劳动参与率要比美国高4%~4.5%,因为休假中的女性仍然算作就业。但美国与这些国家的女性劳动参与率总差距为10%~14%,因此,宽松休假制度在就业测度中的优势只能解释其中的30%~40%,还有更多影响因素等待探索和检验。
新的女性就业生命周期出现了,那么这种发现到底有什么意义呢?年长时“延长的高峰期”意味着当女性步入老年时将拥有更多的工作经验,更多与工作相关的社会角色以及更加陡峭的收入曲线,那么高龄女性的就业率上升就不仅是正在发生的事,而且将是持续发生的事了(Claudia Goldin在其工作论文"Women Working Longer: Facts and Some Explanations”中重点关注了高龄女性就业问题)。
观望了美国女性的就业生命周期,那么这一发现对我们有什么意义呢?文章中提到劳动参与率与社会保障有密切关系。中国经济体制正处于转型期,社会保障体系也处于转型期,以女性为对象的社会保障系统包括生育保险、医疗保险、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等方面。如果女性劳动参与率下降,而社会保障系统资源却严重不足,尤其是劳动年龄的女性由于主观原因不参与就业,将会加重本来就不完善的女性社会保障系统负担,使这种再分配制度很难做到合理公正。
一份早在十年之前的研究发现,我国女性劳动参与率的生命周期呈倒U形,尚不存在结婚、育儿对劳动力供给的影响,不存在M形曲线所示的变动规律(周庆行、孙慧君,2006)。那么随着经济社会的变迁、二孩政策的放开和将在今年出台的延迟退休政策,我国的女性就业生命周期是否也会发生像本文所说的演变呢?尚待下回分解。
Abstract
A new lifecycle of women’s employment emerged with cohorts born in the 1950s. For prior cohorts, lifecycle employment had a hump shape; it increased from the twenties to the forties, hit a peak and then declined starting in the fifties. The new lifecycle of employment is initially high and flat, there is a dip in the middle and a phasing out that is more prolonged than for previous cohorts. The hump is gone, the middle is a bit sagging and the top has greatly expanded. We explore the increase in cumulative work experience for women from the 1930s to the 1970s birth cohorts using the SIPP and the HRS. We investigate the changing labor force impact of birth events across cohorts and by education and also the impact of taking leave or quitting after a birth. We find greatly increased labor force experience across cohorts, far less time out after a birth and greater labor force recovery for those who take paid or unpaid leave. More work experience across the lifecycle is related to the increased employment of women in their older ages.
香樟经济学术圈征稿
“分享”是一种学者的人文情怀,香樟经济学术圈欢迎广大订阅读者(“香粉”)向公众平台投稿,也诚邀您加入香樟推文team。生活处处皆经济,经济处处现生活。如果你或者身边的朋友看了有趣的学术论文,或者撰写了经济政策评论,愿意和大家分享,欢迎投稿(经济金融类),投稿邮箱:cectuiwen@163.com。如果高校、研究机构、媒体或者学者,愿意与平台合作,也请您通过邮箱联系我们。
香樟经济学术圈
本期小编:汪海建
亲爱的读者,如果您从阅读本文中得到启发,或者受益,请您为本文打赏,以感谢推文者的辛苦工作,鼓励她(他)下一期提供更精彩的推文。(香樟打赏直接给每期的推文作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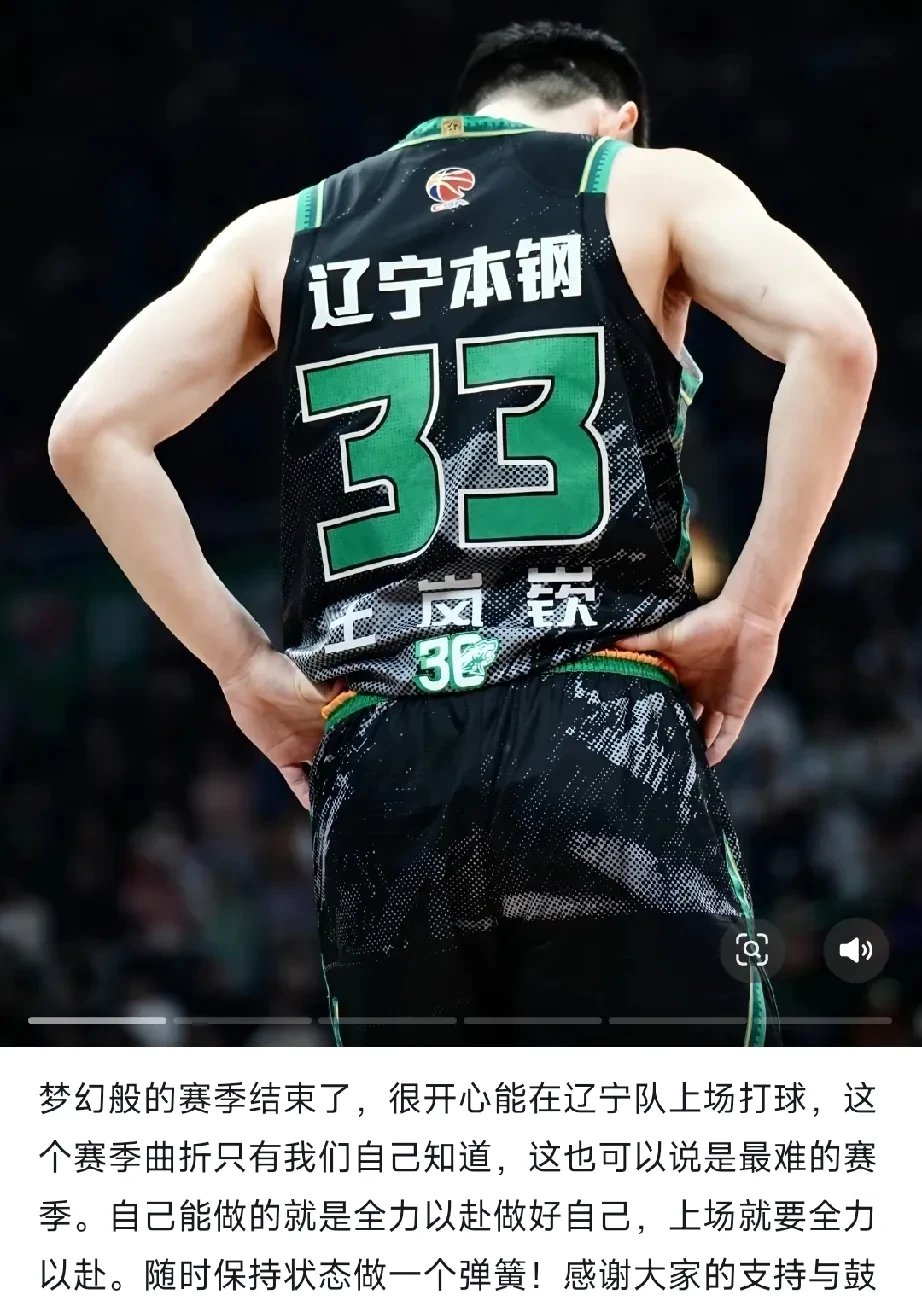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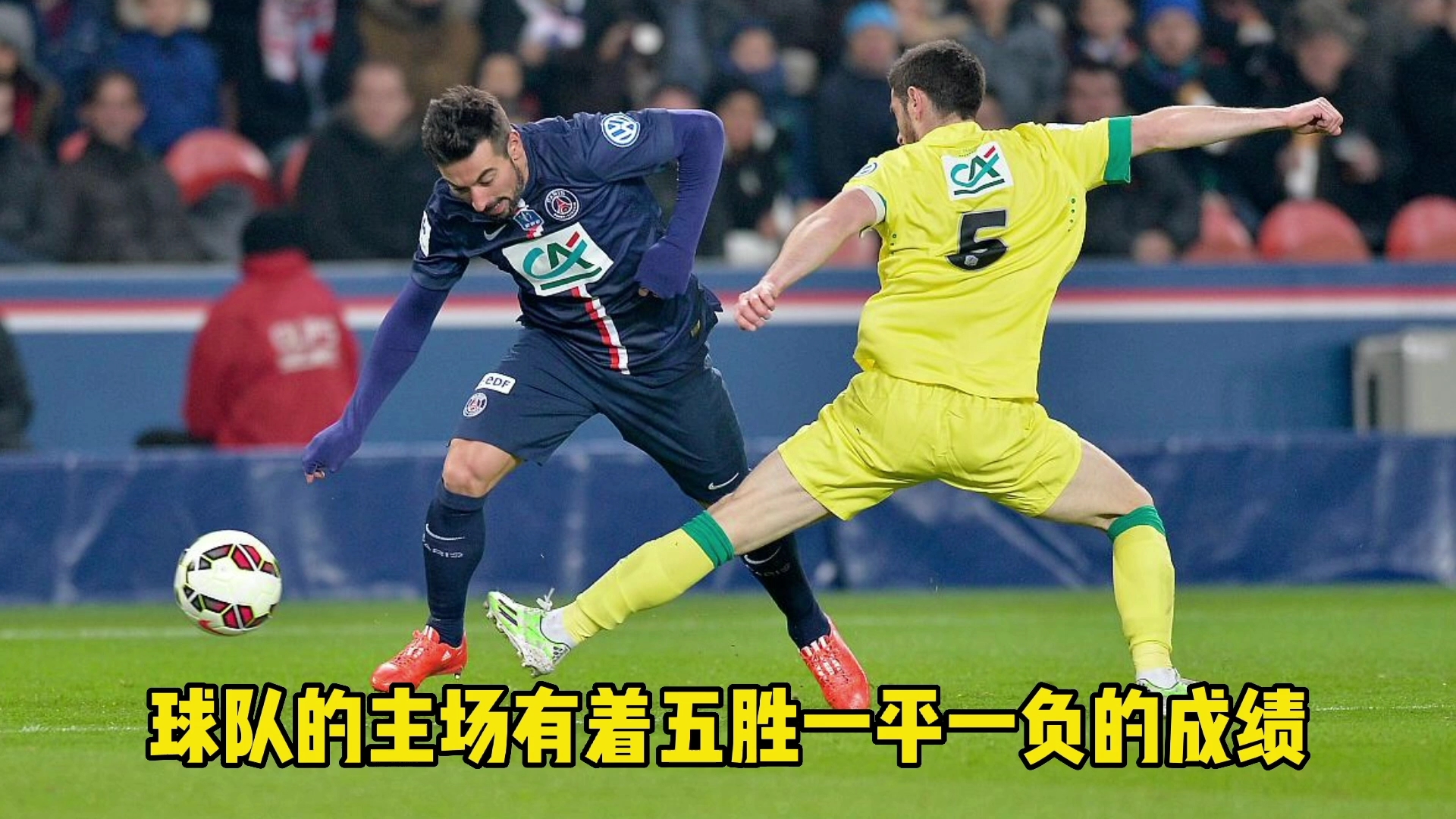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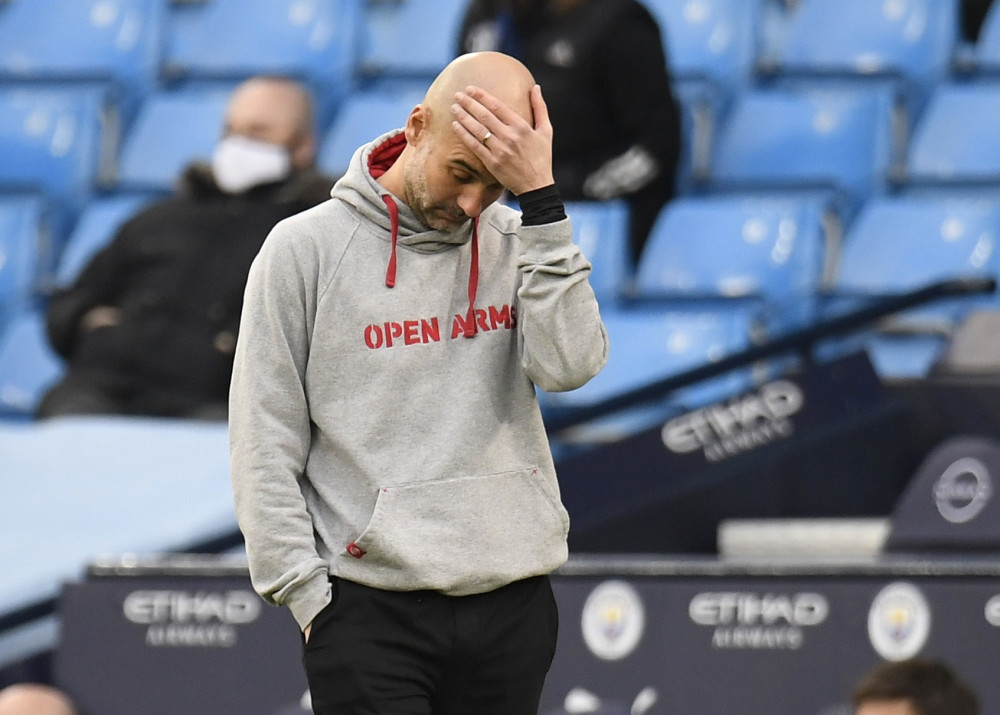





全部评论
留言在赶来的路上...
发表评论